李贺诗歌的死亡色彩
李贺在总体上展现出浓郁的死亡色彩。为营造出此种诗歌特色,诗人在其诗歌中大量使用冷艳凄苦的色彩词、摄人心魄的声响词和变化万千的通感辞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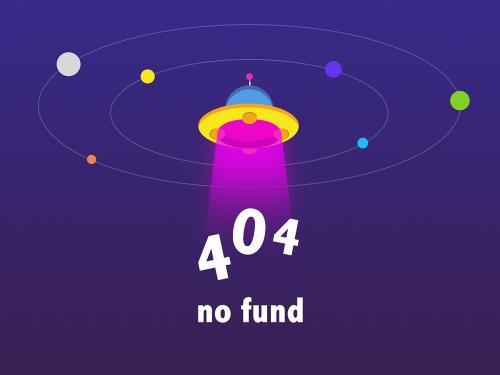
李贺,字长吉,世称李长吉、鬼才、诗鬼等,与李白、三人并称唐代“三李”。他的一生平凡而短暂,命运坎坷,仕途不济,其诗歌大多都在感叹生不逢时和内心苦闷,也都在执着叩问生命本真存在的真正意义,探寻生命的最终归宿和落脚点。正是李贺对生命或者说是死亡的执着追求,才造就了其“鬼诗”真正的价值所在,他描写死亡“鬼境”,通过让人胆战心惊而又触目伤怀的“鬼境”展现出了其诗歌浓郁的死亡色彩。这种浓郁的死亡色彩具体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得以实现:首先,从诗歌的内容上面看,李贺诗歌超越传统的浪漫主义诗风,大量涉足鬼怪、神仙、精灵怪物等等幽僻意象,诗歌超越传统的诗歌诉求,营造了鬼魅幽僻和冷艳俊俏的诗歌意境和描写死亡“鬼境”以期望死亡永恒。其次,从诗歌的艺术特色看,李贺诗歌则表现在字词的选取上,大量使用冷艳凄苦的色彩词、摄人心魄的声响词和变化万千的通感辞格,诗人以其奇异的想象对人间万象、奇幻鬼蜮及仙界进行了生命真谛和死亡归宿的探索。正是由于他从诗歌形式内容的大胆革新求变之举,才成就了他在中国诗歌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李贺诗歌死亡色彩的具体表现
㈠“鬼系列”意象
自佛教传入中原,便因其自身强大的感染力和影响力,成为中国第一大宗教,佛教思想也不知不觉的深入人心,特别是佛教思想中的“人死为鬼”、“万物归为尘土”等等教义深受历代文人墨客笔下留情。李贺便是鲜明的佛教思想影响者,他的诗歌中大量运用到了“鬼”意象。
“鬼系列”主要包括诗中明确写到鬼以及与鬼相关的死、坟、墓、冢等内容。在“鬼系列”的诗歌中,李贺集中表现了三类“鬼”:一是女鬼;二是文士;三是帝王。描写“女鬼”的诗有《七夕》、《苏小小墓》、《春坊正字剑子歌》、《李夫人》、《送秦光禄北征》、《塞下曲》、《官街鼓》等。这些“女鬼”,有苏小小、鬼母、李夫人、王昭君、赵飞燕。写文士鬼魂的诗有:《绿章封事》、《秋来》、《感讽五首・其二》、《自昌谷到洛后门》、《箜篌引》、《》、《许公子郑姬歌》等。这些“文士鬼”,有书鬼、屈原、贾谊、宋玉、鲍照、刘伶、司马相如。描写帝王鬼魂的诗共有4首:《金铜仙人辞汉歌》、《苦昼短》、《上之回》、《昆仑使者》。这些“帝王鬼”,有刘彻、嬴政、蚩尤。除了这三类集中表现的鬼之外,李贺还写了战死沙场的战士:“左魂右魄啼肌瘦”(《长箭头歌》)。又如《南田中行》、《感讽五首・其三》都涉及了“鬼”的描写。
㈡“神仙系列”意象
与歌咏“鬼”意象不同的是李贺还涉及到了道教文化中的神仙意象,李贺诗集中描写的“神仙”大概可以分为两类:居于最高统治地位的神仙和具有一般职能的神仙。于最高统治地位的神仙,有泛指的如: “帝”(《浩歌》)、“天”(《开愁歌》)、“帝”(《公无出门》)、“天公”(《野歌》)、“上帝”(《神仙曲》)、“天帝”(《汉唐姬饮酒歌》)。有指名道姓的如:“紫皇”(《李凭箜篌引》)、“女娲”(《李凭箜篌引》)、“西母”(《浩歌》)。具有一般职能的神仙即掌管某一方面具体事务、掌管某一具体季节、掌管某一具体地方的神,如:“江娥”(《李凭箜篌引》)是掌管湘水的女神,又称“湘神”(《帝子歌》)、“湘娥”(《黄头郎》);“青帝”(《相劝酒》)是司春令者;“羲和”(《天上谣》)是替日神驽龙车的天官;“瑶姬”(《荣华乐》)是巫山神女。
㈢“精灵怪物”意象
李贺描写的这些精灵怪物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吉祥物,即精灵,如“龙”、“凤”、“麒麟”、“驺虞”;一类是不吉祥的,即怪物,如“魈魅”、“毒虬”、、“青狸”、“寒狐”、“木魅”、“山魅”。李贺诗中的精灵怪物有的只是装装样子吓吓人,诸如“龙帐着魈魅”(《昌谷诗》)、“青狸哭血寒狐死”(《神弦曲》)、“百年老�成木魅”(《神弦曲》),而有的就真的是杀人吃人了,诸如“毒虬相视振金环”(《公无出门》)、“狻猊吐馋涎”(《公无出门》)、“山魅食时人森寒”(《神弦》),“毒虬”、、“山魅”等吃人的怪物,正舔着舌头流着馋涎,磨牙吮血,直接危及人的性命。读李贺神仙鬼魅的诗歌,总让人凄切哀婉,甚至毛骨悚然。所以后人有评论说:“李长吉锦囊句,非不奇也,而牛鬼蛇神太甚,所谓施诸廊庙则骇矣”①。
通过对李贺诗歌题材内容和意象情结的了解,我们更多体会到的是他极具哀怨忧伤的死亡气氛。诗人热衷写“鬼诗”,大量营造“鬼境”,就是他死亡色彩的最好佐证。李贺诗歌笔下的鬼境,是黑暗、寒冷、神秘、恐怖的,这是“诗人借以表现他在黑暗、冷酷的现实社会中的切实感受,表达他对死亡的设想猜测、恐惧厌恶,有时也表达他对死亡永恒的期望”②。古人认为,人最终有两种终极归宿,一是死,变成鬼,堕入地狱;一是不死,修成神仙,升上天堂。而李贺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鬼也会死,仙也会死,包括至高无上的天神也会死,所以,在李贺笔下没有不死的事物,死是客观的,一切生命都无法避免。在李贺神仙鬼魅题材的诗歌中,我们看到他将神仙也会长辞与世,比如“王母桃花千遍红,彭祖巫咸几回死”(《浩歌》)、“几回天上葬神仙,漏声相将无断绝”(《官街鼓》)。从诗中看出,李贺对神仙不死这一点是执否定态度的,在李贺的诗中看不到常人对神仙的那种恐惧,更没有敬畏。李贺认为神仙会死,死后也会被埋葬。不仅是神仙,精灵怪物也难逃死的厄运。前文说到李贺诗中的精灵鬼怪有两类,一类是吉祥物,另一类是不吉祥的。在吉祥物中,李贺描写最多的是龙和凤,龙和凤是吉祥物,它们的出现给人带来祥和与安慰,然而,这些原本吉祥的东西,出现在李贺的笔下却并不显得吉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这些吉祥物在李贺的诗中往往是被斩杀烹煮的对象。“曾入吴潭斩龙子”(《春坊正字剑子歌》)、“吾将斩龙足,嚼龙肉”(《苦昼短》)、“烹龙炮凤玉脂泣”(《将进酒》)。其二,这些吉祥物都带上不安的感情色彩鸣叫哭泣。“昆山玉碎凤凰叫”(《李凭箜篌引》)、“老兔寒蟾泣天色”(《梦天》)、“雌龙怨吟寒水光”(《帝子歌》)“凉夜波间吟古龙”(《湘妃》)、“湘江半夜龙惊起”(《龙夜吟》)。其三,这些吉祥物或老或愁或瘦,多数带上不健康的色彩。“老鱼跳波瘦蛟舞”(《李凭箜篌引》)、“老夫饥寒龙为愁”(《老夫采玉歌》)、“黄河冰合鱼龙死”(《北中寒》)。因而在李贺大量的涉足鬼怪的诗歌中,不仅记录了其自身的精神诉求、情感体验和现实向往,还真真切切地表现出来生于王权至高无上的封建社会,其内心必然悲愤,必然借物咏怀,并以“鬼境”或者死亡来展现自己的内心莫大悲痛和苦命挣扎,这便是奇幻鬼蜮给予诗人内心的对于生命本真和死亡意义的探索和寻觅。 二、李贺诗歌死亡色彩的营造技法
李贺诗歌死亡色彩还表现在字词的选取上,首先是字词的选取,大量选用冷艳凄苦的色彩词、摄人心魄的声响词,通过色彩词营造一个冷艳的视觉世界,通过声响词又营造一个幽冷的听觉世界。其次通过变化万千的通感辞格达到视觉世界和听觉世界的交相辉映,诗人放佛置身于难以辨别的玄幻世界之中。通过在字词上面的精心设计和灵活运用,加之李贺才情出众地融合上文提到的意象,使其诗歌始终笼罩在死亡的危险和氛围中,让人不寒而栗,永远都在担心是否“鬼境”真实的存在,又或者是作为生命本体的人是否会沦落至此,更加让人感叹人生的渺小和无助。本来是虚无缥缈的想象物,李贺笔下生花构建了一副不敢逾越的等级制度,顿觉置身之中,却又难涉事外。
㈠冷艳凄苦的色彩词
李贺诗歌色彩词使用相当丰富,出现频率极高,给读者以色彩缤纷、琳琅满目之感。总的的来说,李贺诗中的色彩可以分为暖色和冷色两大类,冷色使用偏多,如白、青、碧都属于冷色类。而属于暖色的词如红、绿、黄等,李贺也将它们进行特殊处理,从而也和冷色一样,染上了凄冷的韵味。如写红色:“谁家红泪客”(《蜀国弦》)、 “九山静绿泪花红”(《湘妃》)、“愁红独自垂”(《黄头郎》)、 “玉冷红丝重”(《冯小怜》)、“芳径老红醉”(《昌谷诗》)、“秋白鲜红死”(《月漉漉篇》)。红色,本来是灿烂热烈的,诗人却让其染上凄苦的色彩,让它与泪、与愁、与冷、与老、与死联系在一起,使得原本灿烂热烈的红色变得凄冷幽暗。又如写绿色:“寒绿尘风生短丝”(《十二月乐辞十三首・正月》)、 “颓绿愁堕地”(《昌谷诗》)、“长眉凝绿几千年”(《贝宫夫人》)。绿色,本来是生机盎然的色彩,但是在李贺笔下,绿色是寒冷的,是颓废的,更是凝重的。对色彩的艺术加工,李贺是有意将暖色冷化,以构成冷艳的.基调。并且为了加强冷色调,李贺还将这些色彩敷以冷光,如“影”、“阴”、“暗”、“昏”等。仅以“光”字使用为例:李贺诗歌中使用光字以冷色调的光为主,如“冷光”、“夜光”、“晨光”、“凉光”、“淡光”、“寒光”,还有冷硬之物体反射的光,如“星光”、“甲光”、“水光”、“剑光”、“露光”、“地光”。冷色彩和冷光线的搭配,就使诗歌显得更加凄苦阴冷。 当代学者罗根泽就写到:“‘冷如秋霜,艳李’,‘冷艳’二字,确可为贺诗评语 ”③。总之,李贺通过色彩和光线,营造了一个极为冷艳的视觉世界,冷和艳本来就是两种互相冲突的风格,所以一般人写冷则暗淡无光,写艳则热烈奔放,很难将冷与艳结合起来而成为一种风格,而李贺却将二者很好地结合了起来,形成了其诗歌独特的冷艳风格。
㈡摄人心魄的声响词
李贺诗歌中声响词,以其幽冷的艺术感染力摄人心魄,勾人灵魂。这些声响词有“啼”,如“春月夜啼鸦”(《过华清宫》)、“左魂右魄啼肌瘦”(《长平箭头歌》);有“吟”,如“雌龙怨吟寒水光”(《帝子歌》)、“鼍吟浦口飞梅雨”(《江楼曲》);另外还有“泣”、“哭”、“咽”等字。值得注意的是,李贺在诗歌中不仅是大量使用带有哀怨色彩的声响词,而且还将带有欢愉色彩的声响词凄冷化。比如“歌”字:“长歌破衣襟,短歌断白发”(《长歌续短歌》)、 “旅歌屡弹铗,归问时裂帛”(《客游》)、“层岫回岑复叠龙,苦篁对客吟歌筒”(《溪晚凉》)。这些歌声不是欢愉畅快的,而是伤感惆怅的。又如“唱”字:“非君唱乐府,谁识怨秋深”(《巴童答》)、“披书古芸馥,恨唱华容歇”(《秋凉诗寄正字十二兄》)、“秋坟鬼唱鲍家诗”(《秋来》)。这里的唱,唱的是满腔怨恨,更甚者有鬼唱的幽怨。再比如“笑”字:李贺诗歌中像正常人一样的笑很少,让人难受的笑则颇多――“缸花夜笑凝幽明”(《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十月》)、“笑声碧火巢中起”(《神弦曲》),此外还有“啼笑”,“强笑”,“讥笑”,“乱笑”,这些笑,都笑出了诗人心中的幽怨凄苦。总之,李贺诗歌中的声响词,都深深地笼罩着“幽冷”的意味。
㈢变化万千的通感辞格
通感,就是将日常生活中的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交织而彼此不分的心理状态。通感运用得好,便会有“你一面读,一面想象着色彩、气味、声音、感觉......可以非常鲜明地想象着它在一首诗歌里体味出许多活的的形象。”而李贺将通感的修辞手法运用得炉火纯青。比如:
“角声满天秋色里”(《雁门太守行》)(视觉通听觉,声音有色彩)
“银浦流云学水声”(《天上谣》)(听觉通视觉,云有响声)
“黑云压城城欲摧”(《雁门太守行》)(触觉通视觉,云有重量)
“海绡红文香浅清”(《秦王饮酒》)(嗅觉通视觉,颜色有香味)
另外,全体通感的,如“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马诗二十三首・其四》),以铜之全体代了马骨之全体,故骨质如铜质,骨声如铜声,马之精神也是铮铮铁骨,从整个感觉的互换来看,李贺将各种感觉打乱再揉合起来,各种感觉相互交错,这可以反映出李贺是如何全身心的投入到对周围事物的体验中去的。中国古代诗歌中,对通感的使用还不是很自觉,故而在评论李贺诗歌时,尤其是遇到通感修辞格的时,能够体会到妙,但是也莫名其妙,说不出个所以然,只能说他的诗“奇诡”,或者说他的诗“语奇入怪”。难怪清人叶燮说:“李贺鬼才,其造语入险,正如苍颉造字,可使鬼夜哭”④。不论李贺诗歌中如何使用大量的冷艳凄苦的色彩词、摄人心魄的声响词,还是运用许多变化万千的通感辞格,诗人都在表明一个永不变迁的永恒主题,那就是对于死亡的探索和对生命真谛的追求。诗人运用娴熟的技巧将死亡“鬼境”的阴森恐怖大肆渲染,浓墨重彩地建构出一副让世人既向往又害怕的死亡世界,无非都是诗歌死亡色彩自然而然的流露和展现。总的来说,李贺诗歌主题内容的选取和艺术特色的驾轻就熟,都在为诗歌的死亡色彩添砖加瓦,表露出诗人忧郁的感伤情怀和营造技法的事故随想,倾诉内心所想所感。
三、李贺诗歌死亡色彩的成因
虽说“诗鬼”的诗歌无论从题材内容,还是艺术特色都极具效法模仿,但还是让人会不明为何李贺诗歌会如此的逆反现实?又为何他会将真实人生溶于鬼境,以求死亡达到灵肉合一?更为何诗人会如此钟爱“死亡”这样一个让人不解的主题呢?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李贺诗歌中呈现的死亡色彩的原由。
㈠孱弱的身心条件
孱弱的身心条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体弱多病;二是性格怪癖。李商隐曾写到:“长吉细瘦,通眉,长指抓”。从李商隐的描述中,我们看到李贺俨然就是一个未老先衰的小老头形象。而在李贺自己的诗歌中,他也反复描述了自己的疾病。诸如“日夕著书罢,惊霜落素丝”(《咏怀二首・其二》)、“归来骨薄面无膏,疫气冲头鬓茎少”(《仁和里杂叙皇甫�》),
“我待纡双绶,遗我星星发”(《感讽五首・其二》)、“咽咽学《楚》吟,病骨伤幽素”(《伤心行》)、“病骨犹能在,人间底事无”(《示弟》)等。总的来看,“糟糕的身体状况,使李贺的五官感受、饮食起居与众不同,同时也使李贺不能拥有正常人一样的生活节奏,不利于他融入群体生活,而他的怪癖性格更使他难以合群,这些因素从现实上否定了李贺融入主流的可能”。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孱弱的身心条件是李贺死亡色彩诗歌形成的内在因素。
㈡不幸的人生际遇
李贺,乃唐宗室郑王李亮后裔。青少年时,才华出众,就已名动京师。在21岁的时候,李贺顺利通过河南府试,获得了“乡贡进士”的资格。但李贺的竞争者毁谤他,说他父名晋肃,当避父讳,不得举进士。李贺怀揣着“兼济天下”的宏愿,希望能够为国尽忠,为民谋福,然而造化弄人,李贺没能考取功名,致使他人生梦想归于泯灭。
在古代中国,儒家的人生哲学一直左右的文人士大夫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文人士大夫们将“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的终极追求。这种主流性的人生追求在李贺的身上无法得到实现,所以李贺“扭曲”了,他不再以一个常人的眼光去看世界,因此,我们在李贺诗歌中看到世界也是“扭曲”的。这也正体现了他诗歌始终难以摆脱死亡色彩的笼罩,一言以蔽之,李贺不幸的人生遭际是造成他诗歌呈现死亡色彩根本因素。
综上所述,李贺的身心条件和人生遭际使他成为了被社会遗弃的“边缘人”,他的边缘处境,铸就了他诗歌始终充满死亡烙印,也造就了“鬼才”诗人李贺的诗风创新和诗歌诉求。
【李贺诗歌的死亡色彩】相关文章:
1.
2.
3.
5.
6.文艺的死亡诗歌
7.
8.